 馆长寄语
馆长寄语
2021年我馆线上推出“换个形式看展览”栏目,分万寿寺历史与文化展、佛教艺术展、瓷器艺术展、玉器艺术展、皇室书画展等九项内容,均计划在十四五期间开放的展览。这批展览以介绍本馆的基本陈列为主要内容,在闭馆期间通过线上形式向观众展示,带您提前浏览北京艺术博物馆的历史与藏品,也有征求各方意见,以便调整修改,使未来线下展览更加祯善不负观众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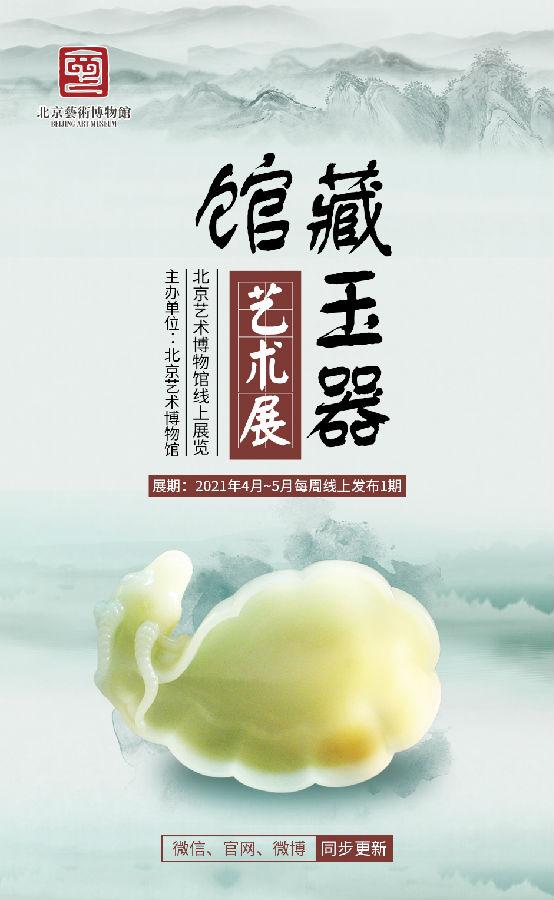
第一章 寻玉之源
第二章 琢玉之华
第三章 用玉之奢
第四章 品玉之雅
第五章 佩玉之趣
第六章 似玉宝石
世俗之美
汉以后,玉的功能继续向装饰性转变,玉雕题材回归现实生活,雕琢的纹饰摆脱了抽象化、程式化的影响。辽、金、元时期,中原汉族传统审美与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文化不断交流融合,玉雕题材钟情于植物花叶、飞禽走兽、山水自然。为了追求更多样的装饰性,玉雕艺术不断吸收外来艺术元素。人物题材的玉雕,童子天真充满童趣,仕女娴静温婉,多呈坐卧姿态,与同时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人物玉雕形成对比,体现了不同的时代风格。

玉发冠 宋 长10.7cm宽5cm高5cm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玉冠表面略带黄褐色沁、土沁和绺,内部残留较多的土。整体如倒置的元宝,减地阳起的两周凸棱绕器而围,打破光素表面的单调感。左右两端有对称的半圆形穿孔,前后两面有对称的圆形穿孔。
经过镂空或掏膛的玉冠饰,一般认为始见于五代。宋代流行小冠形制,可以单独佩戴。宋代的文献里记载宋代玉冠有“栗玉并桃冠”(陆游《老学庵笔记》),“玉龙冠”“白玉九芝道冠”(周密《武林旧事》),“青玉冠”(《宋稗类钞》)。佩戴玉冠的人以皇室成员居多,大体可知玉冠在宋代属于礼仪性饰玉。这些玉冠以男性佩戴为主,女性则主要是巾冠与玉簪结合的佩戴方式,也偶有佩戴玉冠者。

俏色雕奔马纹玉带板 金 长5.4cm宽4.1cm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青白玉质,质地细腻,左下角有裂纹,表面有棕红色皮。带板近长方形,无边框,左上一角略呈圆弧,其他打磨较为平直。正面主体采用剔地浅浮雕手法,正中雕一匹正在奔跑的骏马。马双耳竖起,嘴微张,眼睛圆睁,脖子略向前探出,前蹄双双弯曲,后蹄向后蹬踏,用阴刻线整齐地刻画出细密的鬃毛。马腿关节处突出,马蹄刻画逼真,轮廓清晰。马尾巴向上扬起,体现奔跑的动感,同样施以阴刻线。马蹄下端浅浮雕一排奔涌的波浪,翻起的浪花以未钻透的圆孔来表现,并以排列整齐的阴刻线来表示水的流动。奔马的上方浅浮雕三片云朵,正中的云朵遮住一半太阳。整个画面布局合理,图案丰富且主次分明,琢刻手法粗犷但有矩可循。值得一提的是这件带板还采用了俏色巧雕的手法,奔马的身体、马蹄、马尾都借以棕红色的皮色雕刻,巧妙传神,显示出高超的艺术水准。

玉童子 明 长4.2cm宽2cm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玉料呈黄褐色,带黑褐色斑。童子呈站立状,大头圆脸,梳桃形发,眉、鼻凸起,连在一起,双目呈杏仁状,上身穿对襟袄,下着长裤,衣服上饰阴线刻米字纹,双手握丝带自脑后垂至足边,足边雕一球形玩具,丝带于上方打结。宋代执莲童子的形象深入人心,元、明两代多有模仿的作品出现。馆藏玉童子手握丝带的姿态,以及桃形髻、米字纹开衫等纹饰特征均承于宋代童子,是一件明仿宋风格的器物。
玉中图画
宋代的绘画对玉雕艺术有着深远的影响。传统山水画中的三远式布局与多层镂雕技法相结合,使得一件玉雕作品突破了单一人、物的塑造,而是错落远近景色,将一个场景缩影至寸尺之间。加之圆雕、镂雕、高浮雕等技法的成熟运用,使场景式玉雕营造出多重景致错落分布的视觉效果,具有强烈的立体感。宋元时期流行的立体镂雕有多种表现形式,如玉器纽多见的多层镂雕,表现带饰、佩饰常见的环托高浮雕等。直至明代,镂雕技法逐渐趋于扁平化,过渡到明代中晚期出现了俗称“花上压花”的玉雕工艺。

镂雕鸳鸯荷叶纹玉佩饰 元 直径2.6cm厚1cm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玉佩青玉质,玉质细腻,左下有棕褐色沁斑。形状为周正的圆形,正面镂雕荷叶与两只鸳鸯。正中一片荷叶舒展,上缘与圆环上部相连,细阴刻线刻画出叶脉纹理与芯部,左下的荷叶作枯萎卷曲状,配合棕褐色的沁斑更显逼真,似有俏色的意图,叶片背面同样有细阴刻线刻画出叶脉。荷叶的茎镂雕卷曲在叶片之下,两片荷叶之间雕一对站立的鸳鸯。两只鸳鸯并行,其中一只,头有冠羽,回首背身,双翅并拢于身后,面部、颈部羽毛以人字纹阴刻线表现,翅膀上的羽毛则以平行的短阴刻线表现;另一只在造型上大部分被遮挡住,只有头部和前胸露出,头上冠羽略小,整体作曲颈颔首的姿态。两只鸳鸯并立,好似刚刚游上岸,以荷叶遮挡身体,正在整理羽毛。佩饰背面凹陷无纹饰,也无钻孔,且可以看到打磨的痕迹。整件佩饰虽小,但景物错落有致,层次分明,是一件典型的环托镂雕、高浮雕形式的作品。环托镂雕高浮雕作品始见于金,吉林舒兰县小城子乡完颜希尹墓出土一对鹘攫天鹅玉饰,直径2.4cm厚0.5cm为圆环托镂雕鹘捕捉天鹅的场景,是金代巾冠饰。馆藏镂雕鸳鸯荷叶纹佩也可能是一件巾冠饰,从鸳鸯、荷叶的表现形式看,时代略晚,应属元代之物。


鹘攫天鹅玉饰 金 直径2.4cm厚0.5cm 吉林舒兰县小城子乡完颜希尹墓出土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莲荷鹭鸶纹玉器纽 元 长4.2cm宽3.4cm高3.8cm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器呈馒头形,下琢椭圆形薄底座,有两对小隧孔,其上以多层次立体镂雕的手法装饰莲荷鹭鸶纹。顶部饰荷叶,以短阴线刻叶脉纹。四周刻莲茎,形成多层立面。一鹭鸶尾朝外,扭身伸颈;另一鹭鸶呈立姿,两鹭鸶均身饰疏朗的短细阴刻线。莲荷鹭鸶纹玉器顶流行于宋金元时期,元代玉莲荷鹭鸶器顶更为常见,传世和出土器均可见到。出土的莲荷鹭鸶纹玉器顶在构图上均为顶部琢荷叶,下面有鹭鸶伫立其间,荷叶边缘多内卷,鹭鸶翅膀内侧有方格纹、外侧有细密的阴刻线;主体纹饰和辅助纹饰通过镂雕、阴刻、剔地等不同技法表现。镂雕层次或精致或略简单,其中元大都遗址出土的一件(底径3.7cm高3.5cm)在镂雕工艺上略简单。馆藏莲荷鹭鸶纹玉器纽与之十分相似,确定了其制作的时代。

龙穿牡丹纹玉器纽 元末 长5.7cm宽3.9cm高5.3cm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青白玉质,局部有黄色斑。器底部椭圆形,嵌于一木座之中。整体以多层镂雕的手法雕龙穿牡丹造型。龙昂首,张口露齿,圆目粗眉,长角后伸,发分两股,向后飘散。龙爪为桯钻四孔分出五爪造型,四肢饰网格纹阴刻线鳞片,呈蹲卧状掩身于牡丹花丛中。器身共雕大小各异的五朵牡丹花,并运用叠挖工艺使花朵富于立体感,花叶摇曳多姿,花瓣与花叶细部刻细密阴线。龙穿牡丹是元末明初玉器常见的纹饰组合,多见于器纽、带板等玉雕上。馆藏这件龙穿牡丹纹器顶与湖北钟祥梁庄王墓出土一件金座嵌宝石白玉镂空龙穿牡丹器纽如出一辙,应属于同一时代的器物。梁庄王虽为明代藩王,但其墓中出土了不少元代遗留的玉器,已为学界证实。

龙穿牡丹纹玉带饰 元 长5.8cm宽4.7cm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双螭衔灵芝纹玉镶件 元 长8.2cm宽6cm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青玉质,表面有灰白色沁和绺纹。器物整体作椭圆形,正面略弧凸,以浮雕镂雕法饰口衔灵芝的大小两螭。背面平,中部原有一孔,现已被物填实。双螭身体扭曲,呈伏卧状,宽额宽肩宽臀细身,背部阴刻脊线并于两侧各饰成组双横线,后肢一足在前一足在后,歧尾,一股长一股短,自一后腿下穿过并回卷,四爪尖利。大螭发分两股,上饰细密阴线,以短细阴线刻粗眉;小螭头上光素,以单阴线饰眉。
螭纹是元代仿古玉艺术中的重要表现形式,元代螭纹琢刻时使用砣和圆头细桯钻,在纹饰颈部、腿根部可以看到用“刀”有力,似乎刻断的情况,这使得纹饰在拓片上看如同颈断头掉一般。元代雕刻延续了宋金时期分层为景的特点,主体纹饰琢刻蜿蜒交错,主次分明,立体感强。

镂雕松竹梅双鹿纹带板 明中晚期 长7.2cm宽4cm
北京艺术博物馆藏
青白玉质,略带石质斑点和绺。带板呈长方形,窄边框,正面镂雕双鹿松竹梅纹,纹饰与边框平齐;背面纹饰低于边框,四角有小隧孔,孔内及周围铁锈沁。双鹿站于山石之间,雄鹿仰首,头上长三叉形双角,雌鹿无角,低首翘臀;鹿颈较粗短,身体略瘦长,四肢很细,施重刀,突显尖锥状鹿蹄;脊背和大腿边缘以短而细的阴线刻出鹿毛。竹叶、梅花和松针均取正视面构图,以简单的阴线刻细部。枝头站两只喜鹊,一只前视,一只回首。江西南昌蛟桥公社明墓出土一套同样题材和雕琢技法的带饰,出土时保存完好,为明代中期器物。
馆藏松竹梅双鹿纹带板,内里的纹饰已不再高出边框,这些都与明早期的带板有明显区别。但其与明晚期“花上压花”的工艺还存在差异,采取分层镂雕技巧比较巧妙,将松、竹、梅的主干、叶片、花朵以及部分枝梗雕于上层,与双鹿同处一个平面上;另一部分连接叶子、花朵的细小枝梗则隐于下层,似乎被主体纹饰挡住了,使得整块纹饰有分层错落之感。这种风格属于多层镂雕向“花上压花”的过渡,属于明代中期偏晚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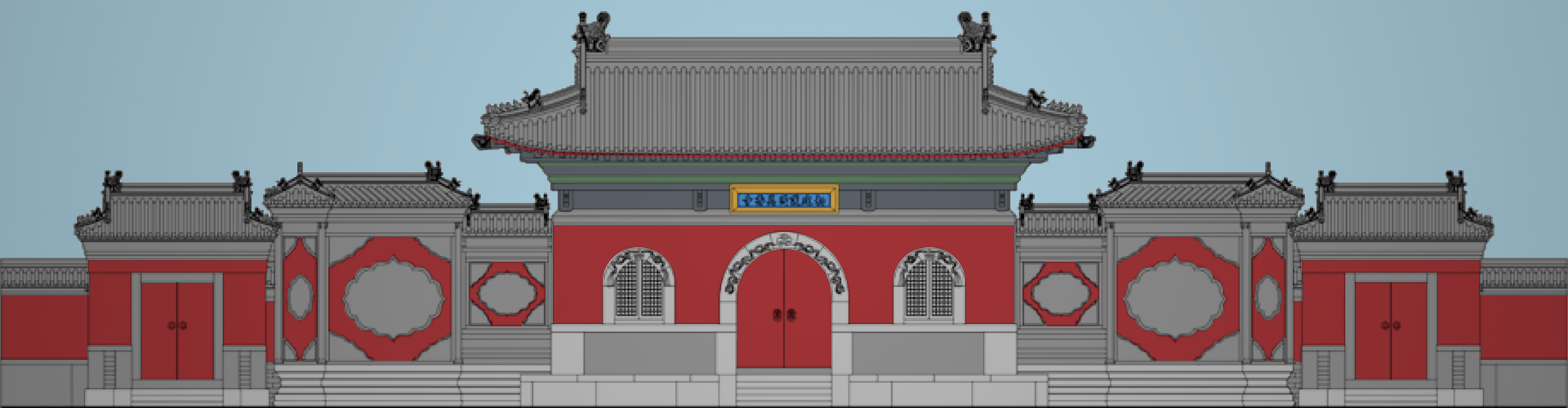





 上一篇
上一篇 返回
返回


